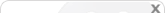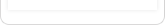豆腐、豆腐皮、豆腐干、豆花、豆漿、腐乳、腐竹等豆制品,價廉物美,營養豐富,老少咸宜,素有“國菜”之譽,是國人愛吃的大眾化美食。自豆制品問世以來,文人墨客對此多有吟詠,讀來頗具韻味。
豆制品中最具代表性且最為普及的首推豆腐。最早涉及豆腐的詩句,出自北宋大文學家蘇東坡《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》。其詩曰:“脯青苔,炙青蒲,爛蒸鵝鴨乃瓠壺。煮豆作乳脂為酥,高燒油燭斟蜜酒,貧家百物初何有?古來百巧出窮人,搜羅假合亂天真。”詩中引出鄭馀慶“清儉重德”,以蒸葫蘆代燒鵝烤鴨待客的典故,借以說明豆腐亦可做成像葷菜一樣的食品,也能亂真,而這正是窮苦的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。
元代詩人孫大雅曾做長詩詠豆腐,其中有詩云:“戎菽來南山,清漪浣浮埃。轉身一旋磨,流膏即入盆。大釜氣浮浮,小眼湯洄洄。霍霍磨昆吾,白玉大片裁。烹煎適我口,不畏老齒摧。”生動有趣地敘述了古代制作豆腐的情景和過程。清代胡濟蒼的《豆腐詩》:“信知磨礪出精神,宵旰勤勞泄我真。最是清廉方正客,一生知己屬貧人。” 不但描寫了豆腐的軟嫩味美,而且寫出了豆腐的精神,由磨礪而出,方正清廉,不流于世俗,贊美其風格高尚。
豆漿又名豆汁,宋傳奇《李師師傳》載:“李師師者,汴京東二廂永安坊染匠王寅之女也。寅妻既產女而卒,寅以菽(豆的古稱)漿代乳之,得不死。”難怪古人對豆漿倍加贊賞:“醍醐何必羨瑤京,只此清風齒頰生。最是隔曉沉醉醒,磁甌一吸更怡情。”
明清時代的豆作坊里常設匾,上書《贊豆皮》詩:“波涌蓮花玉液凝,氤氳疑是白云蒸。素花自可調羹用,試問當爐揭幾層。”崇明廟鎮豆腐干在宋代即負盛名,乾隆下江南時,其先行官到崇明品嘗后留下《詠豆干》一首:“世間宜假復宜真,幻真分明身外身。才脫布衣圭角露,廟鎮俎豆供佳賓。”清人李調元一生寫過不少豆腐詩,詠《豆腐皮》“石膏化后濃如酪,水沫挑成皺成衣”,詠《豆腐干》“近來腐價高于肉,只恐貧人不救饑”,詠《油豆腐》“市中白水常咸醉,寺里清油不碑禪”,詠《豆腐絲》“剁作銀條垂縷骨,劃為玉段載脂肥”。
清康熙八年(1669年),安徽仙源人王致和進京趕考落第,暫以磨豆腐為生。一天豆腐沒有賣完,因時值盛夏怕餿,遂撒上鹽、花椒等腌在缸里。事后遺忘,月后偶揭缸,一股異香撲鼻而來,嘗之鮮美無比,遂創“王致和臭豆腐”牌號,人們無不稱奇,名揚京城。狀元孫家鼐為其號專書二聯——“致君美味傳千里,和我天機養寸心”“醬配龍蹯調芍藥,園開雞跖鐘芙蓉”。
受臭豆腐的啟示,王氏又把豆腐壓坯劃塊,待發霉后再鹽漬,成豆腐乳,用其下酒或佐粥尤佳,不久身價倍增,上了宮廷菜譜。那貢單上有詩為證:“膩似羊酥味更長,山廚贏得甕頭香。朱衣蔽體心仍素,咀嚼令人意不忘。”
豆花,亦稱豆腐腦,也是豆制品家族中的一員,自然也少不了《詠豆花》詩:“瓊漿未是逡巡酒,玉液翻成頃刻花。何藉仙家多著異,靈丹一點不爭差。”制作豆腐的下腳料乃是豆渣,有《嘆豆渣》詩專贊其舍身奉獻精神:“一從五谷著聲名,歷盡千磨涕四傾。形毀質消俱不顧,竭殘精力為蒼生。”潘春華